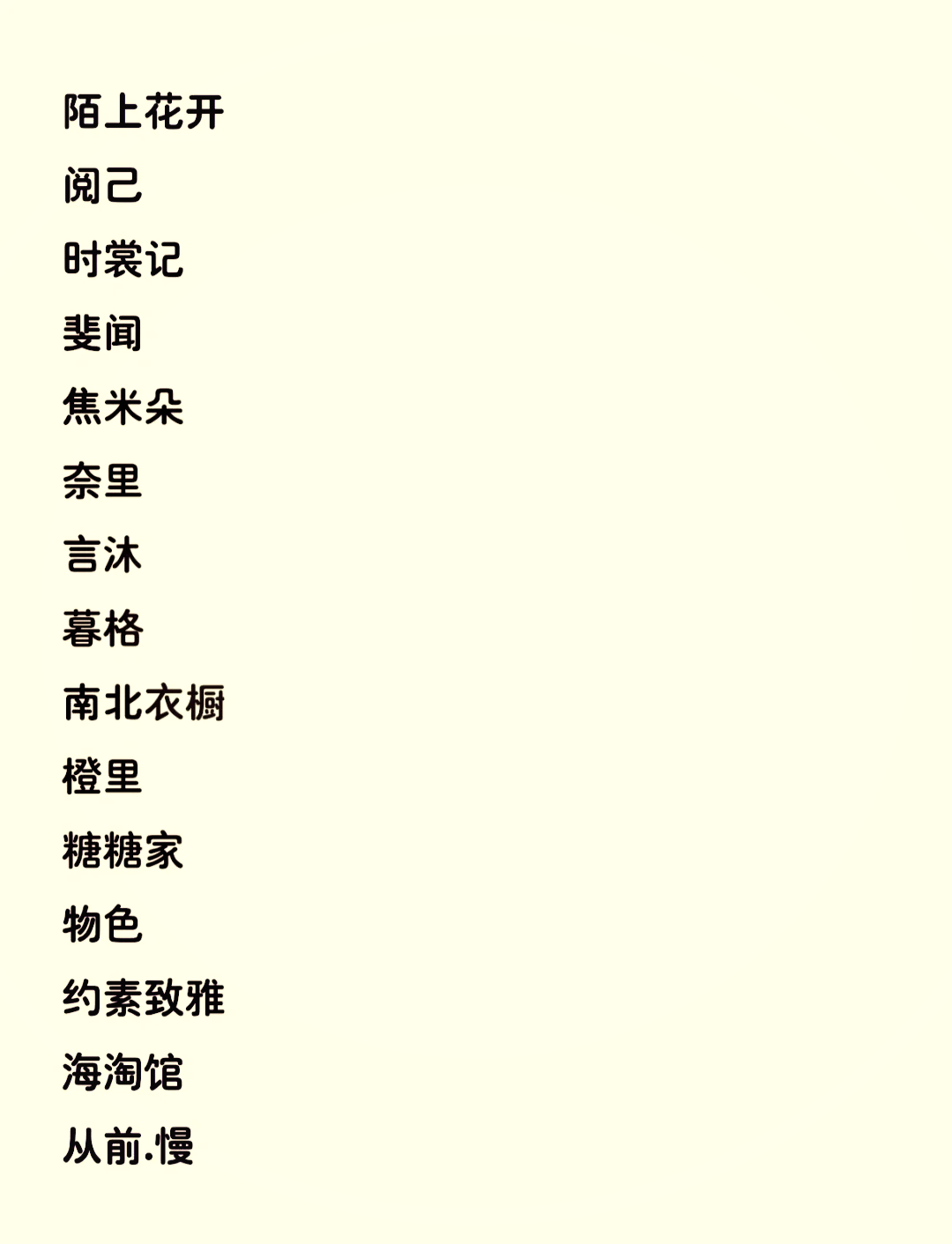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早上醒来,整个朋友圈都被三里屯优衣库试衣间啪啪啪事件刷屏了(还不清楚来由的请自行搜索或脑补)。三里屯,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。一个多月前,周刊君曾经发过一篇由本刊原创的 三里屯夜生活的文章:这里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,任何原始的欲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;这里很多人都是一个人,他们通过与陌生人的亲近寻找慰藉。
来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三里屯——
本文来自第708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有人在三里屯的酒吧里晃了1个小时酒杯,就为了和坐在2米外的异性递个眼神;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男人,他的紧身裤破着好几个洞,头上顶着的黄发挡住一边眼睛,他在拿着单反的街拍摄影师面前来回路过了两遍,终于如愿以偿地被街拍;一个女孩拿着英文菜单,流利地点了一桌西班牙菜,她的英文是纯正的美音,普通话却带着山东口音;北街的酒吧的钢管舞表演,一个裤腰带快扎到胸口的大叔,戴着金丝边眼镜、叉开双腿,举起手机对着空中的女孩拍照。
在4公里以外的北京簋街上,两个刚刚吃完麻辣小龙虾的游客到处问:“三里屯咋走?有没有公交车到?”
三里屯是北京“神奇的存在”。
这个当年因距内城三里而得名的地方,位于北京朝阳区中西部,北京东二环最繁华地段。因上世纪60~70年代,这里建起外交公寓群,三里屯一带逐渐成为驻华外交人员、外国人聚居、购物和外事活动的重要社区。三里屯地域内有10条纵向、12条横向街巷。商业、服务业网点密布,三里屯酒吧街也成为北京夜生活主要场所之一。
北京和“时尚之都”沾不上边,但几个大商场围起来的三里屯,又因毗邻使馆区,传递出一种时尚讯号,聚拢了北京的“潮人”。五颜六色的美瞳、彩色Newbalance运动鞋、MCM铆钉双肩包、皮裤和在冬天也要坚持露出的脚踝……几乎成了三里屯的逛街标配。各种口音不同阶层的中国人,各种肤色的外国人,都能在三里屯碰到。它因此被写在旅游攻略上。
据统计,在三里屯周边3公里的范围内,“扎堆儿”着超过200家的酒吧,占全北京酒吧的40%以上。三里屯也成为夜晚北京最热闹的地方。和三里屯仅1个红绿灯距离的工人体育场完全不同。相距1公里外的工人体育场里总是充满了上万名地道的北京球迷,他们穿着宽松的绿外套,脚踩一双球鞋,用浓郁的“京腔”高喊:“这里是北京”“别装孙子”……更多更直接粗俗的京骂总能激怒全国各地的球迷。
三里屯则是另一个世界。台湾人Tony喜欢早晨坐在咖啡馆享用100元一杯的手冲咖啡,注重“酸碱平衡”的他,每周会在进口超市买齐一周用的饮用水;几个拿着“名牌”包的女孩排了一小时队,终于坐进一个不知道是花店、杂货店、咖啡馆还是甜品店的地方,为了喝至少128元一位的下午茶,9块点心被装在三层的英式餐具中,她们拍照发了朋友圈后,开始担心这些甜品会不会让她们发胖。“有很多有钱人,也有很多人拿着几千块的工资,却总想在三里屯活出年薪百万的感觉。”三里屯一个酒吧老板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14:00 欲望
早晨,一些裹得严严实实的北京大爷、大妈坐在空地上晒太阳。一个住在三里屯幸福三村的老大爷正和修车摊的王伯讨论“京客隆超市”的韭菜到底贵不贵?
三里屯的一天从下午开始。就像省去了前菜的大餐,失去早晨的三里屯从它苏醒开始,一切都是直接和赤裸裸的。
下午2点,编剧小蕾终于找到合适的衣服,准备奔赴三里屯。为了出门,她已经在家准备了4小时,换了数十套衣服。心情不好时,她有严重的“出门恐惧症”。
这天,朋友约她在三里屯的星巴克门前见面,每当她们约在这个地点,小蕾就要“收拾一下自己才能出门”。因为那里每天都聚集着四五个拿着单反相机的摄影师,围追堵截各种“潮人”。小蕾的经验是,“要靠单品取胜,比如帽子、墨镜之类的,街拍没人看脸。”
虽然小蕾通常会拒绝街拍,但能被他们拦下,她还是会有一些“小雀跃”,因为如果不被拦住,那就意味着你的打扮有点老土。不时尚的姑娘在这儿“让人看着心酸”。
三里屯的时尚是从“太古里”飘出来。这是一个大型开放式购物中心,2008年夏天正式营业。这个投资约48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由太古地产全资持有。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,广场上一个宽26.9米,高7.7米的LED屏幕,循环播放着各种广告和商场宣传片。
2010年后,太古里分为南北两区。面积逾7.2万平方米的南区以年轻潮牌为主,这里有在苹果店里蹭无线网给手机充电的年轻人、抹着红唇的街拍达人、在广场喷泉戏水的小孩;一份52块钱的沙拉里面几乎只有生菜,一般坐在那里吃的多是外国人。占地4.8万平方米的北区则聚拢了一批国际高端名牌,但人潮总是比南区冷落几分。
246个商户散落在太古里19座当代建筑中,至少有27个品牌,在这个开放式购物中心聚集了大牌旗舰店、概念店、精品店、北京首家店、中国最大门店、全球最大品牌中心……这里还有一个拥有1700个座位的8屏影院、892个停车位;还有超过30家餐馆和酒吧,和一个99间客房、将近1.6万平方米的精品商务酒店,在那里住一晚1950元起。
有的酒吧每两个月就要更新一次酒单,可一家从未更新过菜品的拉面馆,竟也在那存活了多年。就像一个拥有5辆法拉利的美国人,他喜欢骑着自行车来这里的酒吧喝酒,而他身边是乞丐拿着讨钱的碗,静静地坐着,他的碗里有满满的1块钱。三里屯店和人都是这样,以一种毫不违和的极度矛盾感相互映衬。
2014年9月,90后王宫和妻子派派在三里屯SOHO开设了一家女仆餐厅,同样主题的餐厅北京仅有两家,而在三里屯,这样的餐厅就“毫无违和感”。要知道餐厅所在的商厦,曾使上海小南国这样的传统餐厅黯然撤店。
夫妻俩同是“二次元”爱好者,两人拿着积蓄和父母提供的创业资金,又向银行贷款了150万,开始人生第一次创业。
中午,派派穿着至少3层的女仆裙站在店门口,细声细语地用日语说:“欢迎光临”。一天5000元的流水、两次翻台,足以让这个50个座位的餐厅收支平衡。谈到这些,派派的声线变得底气十足。
笑容甜美的“女仆”桔子用1分钟画了一只Hello Kitty在蛋包饭上,又用10秒钟给蛋包饭“施一个变好吃的魔法”。有人不明白这“魔法”意义何在,但同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40次。17岁的“女仆”安安被称为“店花”,有客人会专程从中关村过来为她捧场。每天至少有10桌客人要求和女仆合影,还有客人会问:“能不能跪着服务?”
“这里会让人的欲望不自觉地膨胀。”派派这样评价三里屯。
夫妻俩经常忙到“全身要碎掉”,因为原来的工作太辛苦,她才辞职创业,原本只想开一家自给自足的咖啡馆,一个月轻松挣几千块就心满意足,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计算:“每天流水达到2万元,两年内就可以开幕一间分店”。
鹤子是三里屯SOHO的上班族,偶尔她的同事们也会光顾这间女仆餐厅。一次饭后,她穿着一件紧身裙等电梯,一个皮肤松弛的外国男人走来,对她说:“一百万一晚。”迟疑了一下,又改口道:“一千块一晚。”这时刚刚下午三点钟。
小蕾凭借一副香奈儿墨镜成功被摄影师拦下,她婉拒了街拍,和朋友们坐进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,开始享用下午茶。
小蕾住在北京青年路的公寓里,距离三里屯大约20分钟车程,她的男朋友戏称三里屯是小蕾的家乡。每次写完稿,她会和朋友来三里屯庆祝,从下午三点到凌晨三点。她自己也想不出除了三里屯,还能和朋友们约在哪?
在三里屯,你可以花11.5万元买一件拿破仑三世的古董盔甲;也可以用48元在咖啡馆买一块2厘米长的村田智明设计的橡皮。

在小蕾用餐的餐厅里,制作一款蛋糕需要20分钟,他们“现点现做”,顾客也乐于等待。营业后的第二个月,这里便开始出现排队人潮,一到周末,大约50个人在店外等待翻桌。自从王菲来这里喝下一碗莓果酸奶,这款52元一杯的酸奶每天能卖出100份。
北京还有哪里可以替代三里屯?几乎所有在三里屯的采访对象都有这样的反问。
17:00“脏街”丢失的灵魂
虽然每晚都有人在三里屯high到呕吐,但这里的光辉正在渐渐暗淡,和后海、五道口等地酒吧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。
三里屯酒吧街最初是为外国人服务的,这里毗邻使馆区,周围又有不少外企,90年代初,热爱夜生活的外国人,在这里点亮了北京的夜空。酒吧街最初分为南北两条,最先兴起的是“三里屯北街”,第一家酒吧“咖啡咖啡”诞生于1995年。
那时的酒吧老板几乎都有海外背景,街上也挤满了来自各国的老外。那时的北街还没有钢管舞,周末像庙会一样人山人海,有的酒吧要门票才能进,人们拿着酒瓶站在路边,彼此没有心防地“瞎聊天”。
先锋的中国人也开始闯荡三里屯。那时作家大仙与何勇、崔健、石康等人并称为“三里屯十八好汉”,他喜欢从北街第一家酒吧喝到最后一家,再从尾喝到头。大仙有数不清的作品灵感来自三里屯。
那时,三里屯聚拢了一批向往外国文化、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。1998年,还是学生的陈璞第一次来到三里屯,爵士、民谣、电音等各式各样的音乐声从风格迥异的酒吧里飘出来。几块钱买一瓶酒,就可以在北小街的各种酒吧串场、跳舞,没有人逼你消费。那时,北小街也没被称为“脏街”,那里还只有一家麻辣烫。在小卖部买一瓶酒,陈璞就能和朋友坐在一家酒吧的院子里,吃着烤蘑菇,聊天到凌晨5点。
那时“太古里”还是一片6层的居民楼,酒吧和外贸服装店聚集在居民楼一层,而那时几乎每个酒吧老板的梦想都是“开一家与众不同的店”。陈璞喜欢在那些外贸服装店买衣服,平价又时尚。她也坚持在冬天露着腿,“这是一件多正常的事,有的鞋就是要露点腿才好看。”而现在的冬天里,更多的女孩穿着“看得见肉的黑丝袜”从豪车中走出来,也有女孩光着两条大白腿坐在酒吧的卡座上,相比之下,只“露脚脖子”的年轻人已太保守了。如今步入而立之年的陈璞已经很少这么穿。陈璞现在很少再走进酒吧,她更愿意在三里屯买衣服、逛精品店、做指甲。现在,她有各种名牌衣物包包,她的打扮更加时尚、精致,也更依赖品牌。
自从8年前,她供职的公司搬来三里屯,她已经离不开这里,“三里屯的变化特别大,但每一个变化我都能接受,因为发自内心地喜欢,所以我把三里屯融入在生活里,毕竟这里还是聚集着同一个调调的人。”
作家大仙在《十年三里屯》中讲述了三里屯的最大意义。“1998,在三里屯酒吧,一位城乡结合部的带头大哥,坐下来就问:咱酒吧有啥下酒菜,炸花生米和猪耳朵有吗?2008,秀水假名牌越穿越像真名牌的私企豪杰,张口就问:洋葱圈有吗?炸泥肠有吗?水果沙拉有吗?里面多搁猕猴桃。三里屯的价值在于,让中国人从吃糠咽菜,一把进步到奶酪黄油。”
如今,这里的餐厅仍大多是西餐,你能吃到意大利菜、西班牙菜、墨西哥菜,还能找到印度餐厅、伊朗餐厅、日韩料理、美式烤肉、英式下午茶……有的餐厅的菜单甚至没有中文只有英文,而常来这里就餐的中国客人也能不看菜单就点菜。他们有的梳着油头、西服革履,在餐厅切一块100g的羊排;有的姑娘从这一路闯进老外圈,成功移民;也有人背着帆布包,在书店翻阅英文的设计书。
现在的陈璞更想要安静的生活,于是她选择和三里屯的中心保持距离,在C5艺术区开了一间咖啡馆,这里距离“太古里”1公里,走过去至少要16分钟,经过两个红绿灯。咖啡馆每天早上10点开门迎客,晚上7点关门,这里和三里屯的夜晚几乎没有瓜葛。下午5点,她坐在自家的咖啡馆,享受着一杯拿铁,里面有两种咖啡豆,加的是一款“奶味很淡”的牛奶,为此她把市面上所有的牛奶都试过一遍。
大仙的三里屯死于2005年开始的一场拆迁。2003年,北京政府出台“新三里屯规划”方案;2005年,三里屯南街、北街开始拆迁;2007年3月,SOHO中国获得三里屯的一块地皮;5月,世茂地产以14亿元人民币收购另一地块……之后它成了后来的“三里屯太古里购物中心”“3.3服装大厦”“三里屯SOHO”和“世茂·工三”商场。
这些地产商的出现改变了三里屯的商业格局,酒吧街的租金至少翻了一倍,三里屯北街原本风格迥异的酒吧几乎变成一个模样。路口的地平线酒吧开始请女孩跳钢管舞,之后几乎每家酒吧都竖起了两根钢管。水烟首先出现在某一家酒吧,不到一个月,这条街上的另外13家酒吧都开始出售水烟。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丁点商机,复制是最简单又低成本的方式。
虽然“脏街”始终是三里屯的“灵魂”,但它的传奇色彩也开始黯淡无光。Jim是这里一家酒吧的经理,在这里工作了16年,在老家他曾是一个厨师,因为喜欢酒吧文化才来到三里屯。最初他是酒吧的服务生,住过地下室;两年后,他变成调酒师,2006年成为店长,后来他和朋友一度在三里屯开到三家酒吧,现在他和朋友在北京拥有两家酒吧和一个餐厅。
Jim今年40岁,孩子刚刚5个月,他和妻子在三里屯相识,是同行。“我们这个行业,找同行最好,能互相理解。”后来,妻子改为白天上班,“女孩长期上夜班很容易老。”而Jim依然要晚上工作,时常顶着太阳下班回家。
他和妻子虽然睡在一个房间,但两人只有周末休息时才能真正见上一面。这样的生活他们已经持续了四五年。“你看我满脸的皱纹,原本想40岁退休,但现在觉得身体还可以,喜欢这个行业就继续做吧。”
他现在痛恨别人把这条街称为“脏街”。“脏街”得名于屡禁不绝的麻辣烫、烤串,半夜会有化了妆的女孩不顾口红来撸几串,也有外国人捧着一碗麻辣烫和一个大煎饼。现在,城管车往路口一停,麻辣烫和烤串不见了,只剩一个煎饼摊半夜坚守在团结湖地铁口。
去年,隔壁卖烟的大姐对Jim说:“这条街真是烂透了。”他们认为这种褪色始于2010年,起因也是翻倍的租金。
为了盈利,三里屯的酒吧几乎只剩下两种:一种以价格取胜;一种注重格调。于是,来三里屯消遣的人们也自动分成两类:站在便利店门口1分钟喝光一瓶啤酒的人,很难和穿着西服、抹胸裙端坐在高大上的酒吧里晃1小时酒杯的人成为朋友。
但这两种人都能迅速在三里屯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在脏街的奶茶店可以花8元买到一杯青提汁,而在相临的太古里的一家饮料店,一杯提子汁要49元。Mojito装在塑料杯里,15元一杯,如果你向北走95步,来到一家酒吧,用玻璃杯里喝下一杯Mojito要花费35元,而在更远的另一家酒吧,喝一杯鸡尾酒要付出70元。小蕾喜欢这间酒吧的鸡尾酒,她有一个固定的服务生,小蕾每次都愿意给她一些小费。
金子早已对酒吧里的各种事习以为常。他从住处步行到酒吧只要20分钟。他的生活圈子非常小,每天两点一线,但又阅人无数。
他不高,有些胖,聊天时,他的烟一直没有断,不时地咳嗽几下,2个小时里,他喝了4杯鸡尾酒,这让他起身微微晃动。
5年前,22岁的金子来到三里屯这家20平方米的小店,服务员、收银员、门外掮客,他什么都做。23岁时,他吸了第一支烟,第一次喝醉,那时的他看不到未来,又企图为梦想挣扎一下。这个不善言谈的男孩喜欢弹吉他,他每天要练琴8个小时,只睡4小时。那时他唯一的梦想是发专辑、组乐队、开演唱会……现在他早已不再想它。

18:0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
下午6点,27岁金子点亮了酒吧的灯箱,他几乎是北街最早开灯的人。
当金子正努力地卖出一瓶30元的啤酒时,他的顾客正在谈一笔过亿的房地产交易。金子形容这些人是“坐着挣钱的”。“我们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,挣得还不到他们千分之一。”
三里屯从来不拒绝任何人,所有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有钱人来这里消遣,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生活。
这里可以让人迅速找到同类,也能把另一部分人消磨成同一个样子,人们不可避免地在这里被同化。
酒吧老板David的微信里大概有2000个“好友”,每个发朋友圈 都至少有50个“赞”。每晚,他看着彼此陌生的客人交换电话和微信,他很清楚有一类客人在“假high”,但他也要向各种客人打招呼,和他们微笑、握手、拥抱、贴脸,称呼他们“亲爱的”。
Paul并不爱喝啤酒,但现在他会习惯性地点上一瓶自己公司的啤酒。啤酒的泡沫在他的胃里翻腾着,这一年多里,他的呕吐物几乎出现在每个三里屯酒吧的厕所里。一杯500毫升的啤酒,他可以轻松干杯,这份工作已经让他胖了10斤,还有了中度脂肪肝。最近,他已开始测试新人,考察他的“酒品”,而他最初的痛苦也传递给了下一个人。
菜菜一直阻止她暗恋的德国男孩来到三里屯,她的外国前男友最初只是一个羞涩的邻家男孩,但在三里屯,每天都有中国女生请他喝酒。“如果每个晚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女孩,为什么还需要稳定的关系?”男孩和菜菜分手后,他身边从来没缺过姑娘。
但三里屯依然能让Sunny每天出门都能抱有一丝期待感。6点半,Sunny骑上电动车,从东四的一个大杂院出发,她要在7点前到达酒吧开始今晚的工作。而这时已经有两个同事在备料,他们要榨出至少9种水果汁。
Sunny是这家酒吧的调酒师,她已经在三里屯工作5年,称得上“阅人无数”。在她眼中,客人只有两类,“装×的”和“低调的”。她几乎能一眼识破前者,有时,她会和同事打赌这样的客人会点什么酒。“很装的人一般会点长岛冰茶,因为这也许是他们知道的唯一一种鸡尾酒。”她至少能猜中70%。
7年前,17岁的Sunny刚刚来到北京。那时,她还是一个在王府井卖糖葫芦的小姑娘,一个月能赚700元,每天往返于宿舍和王府井小吃街,根本搞不清北京是什么样子。但她能迅速打开心扉,在公交车上和一位北京老大爷成为了忘年交,今年春节他们还在一起度过。
5年前她来到三里屯,从酒吧的收银员做起,那时的Sunny还是个慢热的人,她很少主动与客人说话,也不会讲英文。而现在的Sunny会和每个熟客寒暄,开场白通常是:“好久不见,你还在北京吗?最近怎么样?”
她认识5个David、2个Celine、还有数不清的Tony。“这份工作,让我看人看得太清楚,一个清醒的人走进来,走出去的样子千奇百怪。”Sunny在三里屯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,他们都是为了买醉而来,酒吧时光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短暂的休憩,正因为这种短暂,酒吧里的谈话变得不够真实,人们伪装、吹嘘,因为没人在意真假。
至少有70%的客人,Sunny知道对方的名字、工作,但对方究竟是谁,她也说不清。在三里屯,好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,又都不怎么认识。
Sunny最晚会在下午两点起床,上班以外,她几乎都宅在家里,她不喜欢一个人出门,“特别害怕孤独,出门必须要有人陪。”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两年,起因是一次分手,“生活突然变成自己一个人,很不适应。”
但Sunny并不是个娇弱的姑娘,每隔几分钟就能在酒吧的二层,听到她在楼下爽朗的笑声。
现在她的收入涨了十多倍,服装品味也从美特斯邦威变成了Zara,但是她再难对人坦露心扉了,“自己的心和别人拉开了距离。就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事。”大多数情况,人们乐于对调酒师倾诉最隐秘的心事,因为对方是一个和自己真实朋友圈不相干的人。而调酒师的心事很少有人问起。客人就是客人,只有极少数会成为朋友。
21:00 性是一件简单的事
三里屯的夜晚从9点开始升温,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,在某个酒吧落脚,寻找来自陌生人的短暂慰藉。
一到9点,脏街上几家酒吧的音乐会准时响起,这让脏街的声浪瞬间达到100分贝。人们的心脏随着轰鸣的舞曲和电音怦怦跳动。这里有一间名字以K打头的酒吧,提到它的名字,很多三里屯熟人都露出诡秘的笑容,这是三里屯心照不宣的秘密,这个酒吧是大家公认的一夜情“圣地”。
K的舞池能容纳15对“情侣”,他们睁着眼睛在闪烁又昏暗的灯光下接吻,手伸进彼此的衣服,摸索着另一个人的体温,即使你有舞伴,也会有其他人贴近你。一个外国男人对拒绝他的菜菜说:“你不找一夜情,为什么要来这里?”这个困惑只持续了5秒钟,他的眼神便又落在另一个女孩身上。
西西厌恶K的音乐,但为了陪朋友,她还是走进了去。西西不挑酒,能醉、便宜就行,于是她在小卖部买了一瓶5块钱啤酒,藏在袖管里带进K。
西西自诩“文艺青年”,喜欢“亚文化”。她今年33岁,戴一副黑框眼镜,还梳着学生一样的“齐刘海”。她是北京人,有一口浓郁的京腔,一个人住在崇文门的一个60平方米的“城中豪宅”,她喜欢接待世界各地的沙发客,也乐于在旅行中睡在别人的沙发上。她身上有不少文身,一个彩色热气球文在她的右肩上,刻上它“花了3个小时,很痛。”
三年前开始,她常来三里屯,她喜欢和老外们一起站在路边喝酒聊天,“中国人只局限在想一想,而外国人会直接跟你聊天”。她的老外朋友似乎比中国朋友还要多,除了南极洲,每个大洲都有她的老外朋友。“中国人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。我常想,如果把两张100块钱放在枕头下,让它们做爱,第二天会不会生出一张20块钱?”
她愿意和外国人成为朋友,有的成为“炮友”,选择标准是“互相没什么感觉,又能聊到一起,还想再见面,就是这样。”年初,她有个“炮友”结婚了,从恋爱到结婚只用了一个月。她多少有点失落,但“这种关系,大家都很有自知之明,一方有了稳定关系,另一方自然就会退出,犯不着有什么纠葛。”
自从大学开始,西西就是一个“追求自由,活在自己世界”的人。她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,但她“对那些传统的生活没兴趣”,至于为什么,她自己也说不清。
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在国企,但很快她便离开了体制。她热衷旅行,又辞了另一份工作后,成为了一个自由撰稿人。去年她独自走过至少7个国家,一边旅行,一边为旅游杂志写稿,“我就不能让人管着,有人管我就很烦,所以我不能再上班了。”去年,她还看了32本书,75部电影。这些事,她都是在一个人状态下完成的。
小蕾瞧不起那些借着酒劲儿找一夜情的人,也讨厌“端一杯酒晃1小时,其实眼睛都在瞟男人或女人”的人,在她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,也是对酒的不尊重。“如果喝醉后打电话给前男友,怎么对得起这么多死去的葡萄。”她喜欢这句广告文案,更认为酒后乱性只是一个借口,她觉得“把情绪的释放怪在酒上的做法很无聊”。
这时,一个外国人跑上40级台阶来到一家酒吧,他带着刚刚认识的女孩冲进洗手间,朋友们则在洗手间外列队等候,他们踢门、大笑。30分钟后,他们终于开了门,所有人开始鼓掌,两人则像胜利者一样跳着和欢呼的人群一一击掌。
这家酒吧的吧台上有一樽绿色液体,这是Jim引以为豪的鸡尾酒“宝贝睡3天”。它的配方来自台湾,酒精味道很淡,但一杯就足以让一个不太能喝的人“秒醉”。
两个台湾男孩在这里各喝下3杯“宝贝”,其中一个便瞬间瘫在地上,吐了Jim一身。Jim不得不将他们送回宾馆。第二天,喝醉的男生打给Jim询问昨晚发生了什么,因为他醒来发现,自己和朋友赤身裸体地睡在同一个被窝里。接下来的几天里,这个男孩觉得浑身不自在。
这里还曾举办“宝贝”马拉松,参赛者在24小时内喝掉12杯“宝贝”就算胜出,目前只有两个人完成,最高纪录是13杯。他们的奖励是另外12杯“宝贝”。
“不正常”,在这里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Jim所在的酒吧被偷过数不清的摇酒壶和杯子,还有2个灭火器和一个120斤的木雕。也有人偷酒,于是Jim把酒瓶灌满辣椒水。有人刚刚在脏街路口买了一块鸡排,一个人突然冲出来把鸡排打掉在地,又瞬间跑远。这场景Paul至少见过3次。受害者愣在原地,他的同伴笑得前仰后合,没有人去追那个肇事者。
三里屯从来不缺少传奇和秘密。这里有一家著名的廉价酒吧,老板是一对40多岁夫妇,胖胖的丈夫永远在监控室里睡觉,精瘦妻子在收银台忙前忙后。经销商一旦有即将到期的酒,便会低价卖给这个酒吧,这里散货太快了。经销商的仓库隐藏在三里屯西边的一个小区里,这里堆着至少4000箱酒,一箱虎牌啤酒只要80元。
22:00 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
晚上10点,菜菜化着红唇妆,穿着黑色紧身毛衣和牛仔裤,来到一个高端夜店,人均消费超过600元,但通常女孩不用付钱。一个英国男人走过来对菜菜说:“You look so normal here.”(你看起来太正常了)因为大部分女孩穿着紧身抹胸裙、高跟鞋,每个女孩跳舞的动作都很谨慎,她们缓慢地扭动出婀娜的曲线。
穿着西装的男人们在卡座上开了无数瓶香槟,陪坐在侧的女孩依然坚持着在冬天露出两条又白又细的长腿,但他们不跳舞也不讲话,大多数时间是在看手机。
菜菜一边喝啤酒一边聊天,说几句就会哈哈大笑,有意无意地显示一下自己和酒吧老板很熟。她并不是很能喝,3杯鸡尾酒就能有些微醺,她不喜欢廉价的天堂酒吧,因为“那里的厕所实在太脏了。”她说话偶尔夹杂几句英文,纯正的美音,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。她的打扮和舞蹈与欧美女孩没有分别,度假时也不会刻意防晒,认为那是“美黑”。
菜菜刚来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三里屯。那时,她被一家知名服装公司派到北京培训,和一个同事住在团结湖的酒店里,但她觉得孤独,因为“谁没事会和同事做朋友”。她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,几乎每天都被老板“人格羞辱”。
菜菜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强,她不愿意白天被骂,晚上就在酒店早早睡觉,她要为情绪找一个出口,她发现“去人多的地方心里会好受一些”。
每晚下班后,她就会坐着公交车从世贸天阶去三里屯吃饭,最初她经常自己独自买一个披萨边走边吃,或者一个人在路边吃麻辣烫,后来她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一个人,于是就开始主动和别人聊天。
一次,菜菜拿着一个鸡蛋灌饼走在三里屯的路上,一个德国人走过来问她在吃什么,菜菜主动给他尝了一口,之后他们就坐在咖啡馆里,聊了三个小时,至于聊些什么她早已记不清楚。她只是记得,有人陪的时候,生活不会那么寂寞和无聊,哪怕那只是一个陌生人。
那时,她也和男生回家,光着身子躺在床上,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后来,菜菜在一次外地旅行中开始了第一次性体验,“那简直颠覆了我的想象,我要把23岁以前浪费的时光补回来。”三里屯的“性”就像大麻一样,一旦开始就会让人上瘾。
回到北京后,这个身高1米57的女孩站在椅子上和1米95的德国帅哥亲吻,一年里,她在15个陌生人身边醒来。“我只是想要帅的男生。”在三里屯,菜菜亲吻了数不清的嘴唇,分别和两个男生恋爱,可两份爱情都只保持了1个月。
来这里的外国人也深谙三里屯各取所需的交易,早已难再付出真心。菲律宾人Peter是三里屯的典型玩咖,一个晚上,这个满身肌肉的男人可以把3个女孩带离酒吧。
23:00 比小说还荒谬
千姿百态的狂欢日复一日,人们似乎能在三里屯找到另一个自己,这里成了他们平淡人生中的一次超级冒险。
荷尔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跳跃,当酒精和音乐清空人们的大脑,一些人便获得了白天找不到的存在感。每个月,三里屯的酒吧和夜店要举办数不清的派对,酒吧老板David把一位熟客叫做“派对女王”,因为她不会错过任何一场狂欢,她喜欢把外国帅哥照顾得无微不至,甚至车接车送。她是在三里屯发现有人需要她。白天,她是一位30多岁的高中计算机老师。
晚上11点,新来三里屯酒吧半个月的服务生向军,第一次见到客人跳起钢管舞,那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,她的五官在闪烁的灯光下模糊不清。舞台上只有她一个人,在疯狂的音乐声中,她的舞蹈才显得不那么尴尬。这时,终于有一个女孩跳上另一个酒吧那个将近1米高的舞台,她穿着紧身豹纹吊带裙,在10秒内甩了25次头发,这时音乐已经达到125分贝,聊天变得不可能,但也没人在乎是否要开口讲话。
酒商Paul已经喝下4升啤酒,吐了一次,他希望能卖掉2000箱啤酒,让酒吧经理和他签下一张20万的合约。与此同时,“脏街”路口的桔色成人用品店5分钟内卖出了2254元的性用品。
在酒精的作用下,荒诞的气息在三里屯蔓延。有人带着女朋友来到酒吧,却和另一个女子发生了关系。有人来这里捉拿“小三”,却发现自己和“小三”都不是原配。小蕾目睹了这些荒诞的故事,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写作灵感。这里的故事远比她笔下的小说和剧本荒谬、失智得多。
为了收集素材,小蕾愿意请一些陌生的“漂亮女孩”喝上一杯,听她们讲述自己复杂又极其简单的情感故事。“她们的痛苦,几乎都是因为价钱没谈拢。她们似乎对生活有所误解,以为灯红酒绿才是人生的繁华。”
在一些酒吧昏暗的灯光下,尽管每个人的表情都难以辨认,但他们的精神又深层相似。在一家高档酒吧的一个卡座上,至少坐着5个长相极为相似的女孩,她们有着几乎一样的尖下巴、大眼睛和饱满的双颊。“这些整过容的脸上,欲望更加明确,她们所有的快感都来自于钱。”
小蕾抽了一口烟,讲了一个从“外围女”口中听来的故事。一个刚刚拿到一笔遣散费的工薪阶层,每晚在三里屯挥霍。10天后,他变成熟客,和其中一个女孩开始了短暂的包养关系,一个月他要付出3万元。而女孩没有想到,这一个月竟会如此“辛苦”,因为男人要求每天见面。其实,这3万元对男人来说是一笔大开销,他希望“物尽其用”。而“一般包养一个月只需要见面三四次,他居然天天有空。”这场交易让双方都觉得亏了本。
2005年,三里屯派出所开始打击三里屯附近的站街女。如今,更多的漂亮女孩变成了“外围”和“嫩模。”在这里,包养关系可以飞速建立。在一家灯光明亮的餐厅里,一个男人一边打量一瓶红酒,一边问站在旁边的女孩:“多少钱?”女孩面无表情地说:“5000块跟你走。”
三里屯恰好能满足一些女孩对金钱的虚荣和攀比。想买一个名牌包,一个夜晚便可以找到男人付款,性是她们最低的成本。
当一些事可以用金钱衡量,三里屯也变得越来越直接,少有羞涩,甚至有人不再费尽心机搭讪漂亮姑娘。酒商Paul走在太古里的东侧,5分钟的路程,他被拦下两次。“大哥,想不想喝酒有妹子陪?只要200块。”在一晚无数次拦截中,终于有两个台湾人被说服了,结果他们只喝掉5瓶啤酒,一个穿着吊带背心的女孩就要求他们付款5000元。
龙哥负责给工体和三里屯的夜场摆平麻烦,他手下有一批保安,一个酒吧需要付他1000元才能叫来一个保安把闹事的客人送出门外。
在三里屯,高潮与失落同时发生,各种情绪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。酒吧经理Jim举办过数不清的狂欢,也举办过难以统计的离别派对。几乎每天凌晨都能见到在街边呕吐的男人,瘫倒在地的女人。冬天,三里屯派出所的民警会把醉倒在地的外国人带回警局,让他们睡一晚再离开。现在,三里屯北街的酒保们统统戴上了“朝阳区治安志愿者”的红袖标。警察给他们开了两次会,让他们戴上了这块红布。
一段时间里,每周都有朋友在Jim的酒吧宣布离开北京,从此这些人将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,这样的告别也让40岁的Jim流下眼泪。“有个朋友在北京8年了,现在说走就走,这辈子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。”
金子今年才27岁,已经觉得生活无望,现在的每一天“纯粹是为了过日子”。5年来,他至少有7个朋友相继离开三里屯,有人开始朝九晚五的工作,有人回老家做起小生意。“他们想过正常一点的生活,但三里屯给不了他们,这里好像有今天、没有明天。”
平时不愿意出门的调酒师Sunny最近报了一个拳击训练班,逼迫自己出门。每周她有三个下午的课,两小时的拳击训练,让她又认识了另一个世界的朋友,她觉得很放松,“来这里上课的人就是为了放松、锻炼、发泄,同学之间没有顾虑、没有利益冲突,也不用思考彼此的关系。”在这里,她不需要和别人客套,还能揍别人。
现在,西西更愿意去鼓楼的酒吧,那里有更优质的音乐和更有趣的外国人,而且“大家都不装”。她几乎不再去三里屯,因为“那里的人不在乎音乐,只在乎姑娘好不好看、性不性感,目的性太强。”
2:00 疲惫的凌晨
三里屯拥有全北京最长的夜晚,挨着的团结湖地铁站23点45分开出的末班车,永远等不到最后狂欢的人潮。
但有时你能隐隐感受到整个三里屯陷入疲惫。外国人也在聊和中国人一样的话题:雾霾、房子和物价。他们学会讨价还价,不再给小费。王伯的修车摊摆在脏街路口,平均一天会有两个外国人,用中文对他说:“便宜点儿。”
凌晨,在三里屯趴活的出租司机会带走这里的人群,他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呕吐、千奇百怪的痛哭和莫名其妙的尖叫,有时他们会对深夜离开的漂亮女孩开句玩笑:“你下班啦?”即使她是一个正经女子,也懒得做出解释,你是谁在这里根本不重要,也没有人会记住你。
夜半时分,一家酒吧的两个钢管舞女来到吧台,每个人拿走200元,9点到12点她们要表演4 场钢管舞。苹果店的保安终于可以坐下来,用iPad3玩斗地主。凌晨2点,另一家酒吧开始了最后一轮接单,一小时后,这里音乐骤停,灯光打亮,客人的表情还没来得及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明亮,一丝惊慌和失落在他们脸上稍纵即逝。这时Sunny已经工作了8小时,她和另外3位调酒师至少做了600杯鸡尾酒。
小蕾也有些醉了,她想起海子的一首诗,《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》里的那句:喝醉酒时,酒杯很安全,心很安全。
这时候,一家廉价酒吧已经卖出240瓶青岛啤酒,700杯Mojito,6袋垃圾摆在这家20平方米小店的门口;在125分贝的音乐声中打瞌睡的向军终于下班。Paul拖着醉倒的朋友企图为他在三里屯找到一间宾馆,但在三里屯1公里内聚集的超过1200家大小宾馆几乎全部客满。最后他把朋友放在一个简陋招待所的地下室。
这时,一个黑人递给小蕾一根“烟”,她吸了两口后直接晕倒,男朋友不得不把她扛回了家,那原来是一种烈性大麻。
凌晨5点,一个穿着黑色吊带裙的女孩正在等待出租车,她在零下5度的气温中瑟瑟发抖,她的羽绒服在三里屯至少被偷过两次。这时,菜菜正悄悄离开一个陌生男人的家,她要赶回老家的航班,在那里一切都和三里屯不一样。
早上7点,一个女孩戴着墨镜来到24小时营业的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,她没有地方卸妆,眼线、睫毛膏、眼影在眼皮上洇开,宿醉带来的头痛正帮助她记起昨晚的狂欢,而2小时后她就要穿好正装坐在国贸的办公室里。
下午2点,Paul的朋友渐渐苏醒,昨晚发生了什么,他已经完全记不清。
(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)
转载请注明:常州茗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靓衣网 » 潮流女装 » 白总女装(白总是谁)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B5编程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